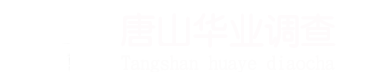就侦查应用而言,启动侦查、实地勘查、侦查询问或讯问等侦查环节都以犯罪要素及结构为对象或依据。同时还有以下侦查价值:
(一)为案件性质推断奠定基础
案件性质即案件本质,是指某类案件区别于它类案件的基本特质。某类案件(某一犯罪类型)既有其“形”又有其“性”,犯罪结构同样如此。基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犯罪结构类型之一的犯罪类型结构反映犯罪的类型性:有什么结构方式就有什么犯罪类型,也就相应有什么犯罪性质。不过,同为犯罪类型,法律定型是法定要件或与其吻合的犯罪类型;侦查所谓犯罪类型是处于自在状态、作为被评价对象的犯罪类型。后者犯罪性之有无及程度,侦查初期由犯罪概念结合立案标准衡量。
依据法益侵害确定案件大类后仍需继续区分。但侦查之初,案件事实残缺不全,侦查人员只能凭借已知事实回溯未知可能。先将某一未知事实类型化,某类案件如杀人,动机目的是未知项,可能为财杀、情杀、仇杀等,若为仇杀又可能是激情杀人或预谋杀人等;其他未知项(暂不包括犯罪人特征)依次类推。逐一区分后再尝试与已知事实对接、逐项检验。当然,类型化也非漫无边际,要同时兼顾理论区分度和侦查实务需要。
要素、类型要素反映案件类型性。仅杀人类型,有关专著就从不同动机目的、工具、行为方式等方面区分为二十四种类型。 其间特定联系反映并制约案件类型。如,同为抢劫,先夺命后侵财(抢劫)和先侵财后夺命(转化型抢劫)也为不同类型;又如,某女在非威逼绑架而至、较偏僻的野外场所被害,多为情杀;再如,结伙犯罪,若结伙仅为致残或致死特定人而无其他目的,除偶发事件,不得排除雇佣可能;等等。从案件类型中,侦查可获取新信息。如,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因矛盾冲突激化、具备毒物来源及载体和使用毒物知识、有合法身份掩护和隐蔽投毒条件、由加害人投毒而至被害人被害的情形,這一特定类型中隐含的内容可揭示侦查方向、范围。
需提请注意的是:学科研究一般以犯罪既遂即同时满足包括过程和结果要素在内的全部要件要素为理论预设;但因多种因素干扰,现实犯罪半途而废、一无所获的情形多有存在,推断时不可顾此失彼。如,本欲抢劫,人已被害,却因故未达犯罪目的,不管法律如何定型,侦查不可仅推断为杀人类型。同时,不要放过如侵害对象错误、练胆杀人、以杀人为手段骗取保险金等例外情形。
总之,无论结构内要素如何类型化及关系如何,案件类型均由基本结构相互关联的七个环节生发而成,从而形成性质互异、千差万别的个案。
(二)为侦查途径选择提供依据
所谓侦查途径是指为发现犯罪人而将犯罪事件与嫌疑人联系起来的路径,包括某一或某些关联两者的犯罪信息、线索、证据。选择侦查途径即从多种备选途径中按侦查原则优选路径。侦查虽受法律规制却是科学的,侦查方法既非多到随意选择也非少到无可选择。犯罪总要与环境发生作用,从而产生物质(信息)交换或转移、留下蛛丝马迹,它的这一特性,为侦查提供了客观条件;物质(信息)交换或转移的程度和侦查获取犯罪信息的能力,决定了案件侦查的难易程度和侦查效果。从已暴露的犯罪结构环节或要素入手,采取必要措施或手段循序渐进地开展侦查,可以开辟相应的侦查途径。 基于要素多方面、多层次,位于多环节,存在若干种关联形式(排列组合),不过,对备选途径可操作性和多管齐下可能性要做恰当评估。同时,除多功能要素外,要注意区分关联对象,与嫌疑人直接、间接关联的犯罪信息一旦被查获,就构成了有效、有时甚至是十分便捷的侦查途径。具体途径有:由物到人、由人到人、由事到人等;由结果到工具、由工具到使用或持(所)有人等;嫌疑人归案前后都可由人到事;一案几个现场和系列案件,现场与现场、案件与案件之间同类要素或组合要素的同一性或相关性,是关联现场、串案并侦的前提条件,还能为发现并认定嫌疑人提供更多线索或证据;大数据时代,能为直接获取嫌疑人或其他要素及其关联信息,提供海量电子信息资源。
(三)为证据体系构建准備框架
证据体系由系列证据构建,是证明犯罪结构各环节及其关联事实的系列证据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阶段和发现嫌疑人阶段方向相反,是对嫌疑人与犯罪事件关系的进一步确定。提请逮捕前,需先行梳理证据材料,使案件事实由证据体系证明。案件事实分为程序法事实、实体法事实两部分,它们都包含若干层次。就定罪量刑实体法事实而言、由低到高层次上包括:具体事实,即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体案件事实;结构事实,它是对具体案件事实的第一次抽象,是案件事实的框架;证据事实,是经核查、检验鉴定等人为提取、复制的案件事实,有自然事实不等于有证据事实,证据事实需经侦查才能发现、提取并转化,同时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又不尽相同,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事实才是案件事实;构成要件事实,它比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系统和抽象,较法条规定的法律事实又缜密和具体,位于两者之间;法律事实,即刑法规定的犯罪规格、标准,是最抽象的案件事实。案件事实的传统分类应予细化。
那么,凭借哪一事实构建证据体系?有人认为,构成要件是构建证据体系的依据。若先以前者构建后者、再以后者去给前者衡量,结果只能是构成要件与其自身的同一。如此循环论证,岂有不符合之理?怎能发现两者差异,发挥后续程序纠偏、纠错功能?它既是形式类型又是实质类型,又如何避免有罪推定?况且,目前的理论模型不无问题。四要件论:将犯罪行为人与行为、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符合辩证法;但又再次综合,将原本六个环节相连的构成要件归并为同样相连的四个组合,转换要件称谓,若将连带权益的对象视为客体,则客体前后都有客观要件,一并归为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之后如何排序?再者,主观方面要件有犯罪性,而总体看被害人心理与犯罪人心理倾向相悖,不顾及前者或将两者合并为一个要件都有不妥。阶层论: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的犯罪类型; 但从结构角度考察符合性前构成要件:一方面以行为为模板的构成要件见事不见人;另一方面后期增补的主观要素如何与既有客观要素衔接?
预防取证疏漏、脱节,方法之一,是对案件事实具体内容做出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第六十四条规定了案件事实的十个方面内容,逐一核查就意味着查清了案件全部事实。分析规定内容,与其说是构成要件的具体化,不如说更贴近犯罪基本结构,是犯罪结构有意无意的运用。规定中,除一个条文涉及程序法事实外,其余则完全可以被犯罪结构相关环节吸收、融入犯罪结构中。如此,掌握了犯罪结构及其内容,对实体法案件事实也就无需做专门规定或做特别理解了。证据体系构建不是“迎上”而是“合下”:案件事实价值自含(决定价值的内容并非外部赋予,仅不过作为被评价对象,其价值若何、是否包含正当化事由等尚待庭审评价),构成要件亦然(征表违法可责,本文支持将所谓消极构成要件要素理解为提示性规定),虽也用之于暂定罪名,但因侦查主要是提供事实而不是提取价值,因而此时不可也不必动用构成要件。由证据体系证明的案件事实最终都要接受法定要件检验、被成立条件格式化,姑且不论下一步如何操作(含定罪逻辑顺序,归刑事法学讨论),侦查构建证据体系先要“眼睛向下”、与低层事实一致。具体事实虽然生动、鲜活却也散乱、零碎,证明案件事实无需也不可能证明案件的每一细节。证据事实仅需与结构事实吻合,都有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不遗漏所有环节及其关联,以及每一环节都不是孤证,就能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犯罪结构同样集形式、内容于一体,是有广度、深度和逻辑递进关系的结构体,结构事实是具体事实向证据事实过渡的中介,以犯罪结构为依据,才能使单一证据组合而成的系列证据有机勾连为链状且实然的证据体系。不同类型案件由不同证据体系证明,构建证据体系尚需依据某类案件类型结构,而类型结构仍是结构、是派生的犯罪结构,证据体系由犯罪结构构建。
华业唐山侦探公司拥有专业的唐山私家侦探,唐山私人侦探调查团队,提供唐山婚姻调查,唐山外遇调查等服务,成立多年博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是值得点赞的唐山侦探公司。了解更多服务请登录【官网】http://www.tszhentan.com 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