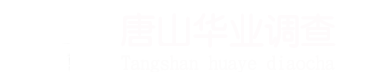当前中国隐私权的保护模式主要以秘密说理论为指导,凸显脱机时代的特色,信息公开后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更加便捷化,容易使公开的信息陷入失控状态,给隐私权利人的生活带来无尽的困扰,原有的隐私权保护模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立法必须适时作出改变,以控制权说为指导,加强主体对隐私利益的控制权,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六度分隔理论,对公开的内涵做扩大化理解,明确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特有的侵权责任,以最终确保隐私权设立的目的得以实现。
隐私权设立的目的性分析
隐私权最初创立于1890年,由美国学者沃伦与布伦迪斯在《哈佛法律评论》发表的《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acy)一文中提出,该文指出,隐私权之所以值得保护,是因为它体现了个人的自决、自我控制、尊重个性和人格发展的价值。[1]隐私权提出时,美国正处于工商业蓬勃发达时期,工业化都市生活死板、乏味,有赖于报纸的信息,以满足一般人对上流社会生活好奇的需要,因而黄色新闻猖狂,令被报道者不堪其扰。[2]因此,隐私权在设立之初,就带有维护个人安宁及自由的目的。虽然隐私权至今发展已逾百年,但此目的仍未有改变,并随着隐私权在各地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新的目的。就中国而言,隐私权设立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维护个人安宁生活权的需要。所谓的个人安宁生活权,主要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维持安稳宁静的私生活状态,并排除不法侵扰的权利。[3]享受生活的安宁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且也是从事其他行为的前提条件,因而维护个人的安宁生活权意味着,对于可能影响自然人生活安宁的信息,在未经自然人同意的情形下,第三人不能予以公开、传播,否则将要承担侵犯隐私权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肖镇诉陕西《收藏》杂志社侵害隐私权案”1对此目的有所体现。
第二,保障个人自决权的需要。如前所述,沃伦与布伦迪斯在提出隐私权时就指出,隐私权对于保障个人的自决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人自决是人格尊严的应有之义,也是个人发展个性的前提条件。个人自决意味着,个人对其私生活领域的各项事务的支配,并能够排斥他人的干涉和妨碍。[4]个人只有能够自主地决定其信息利用,才能避免自己的一举一动为他人所知,沦为社会的“透明人”,最终造成自由权利行使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谢薇诉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隐私权案”2对此目的有所体现。
第三,塑造人格的需要。信息对于塑造人格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人获得信息的多寡将会影响信息主体在社会中的评价,例如在轰动一时的“王菲诉张乐奕名誉权纠纷案”中,原告王菲的婚外情信息因被被告张乐奕肆意传播,导致其被得知此事的人批评、谩骂,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3。因此,信息主体为了保持其良好的形象,对于一些信息而言其一般不愿为不特定的第三人所知。而隐私权所要保护的,也正是这部分不愿为人所知的信息。诚如一些学者所言,隐私权是抵挡贬损个人认定行为或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的权利。[5]
中国隐私权保护的传统进路
(一)传统隐私概念的界定
隐私的概念自产生以来,历来存在着争议,迄今尚无统一的定论。中国隐私权的发展历史较短,在法律的规定上,最初规定有隐私的法律文件为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对于独立的权利规定而言,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才首次明确隐私权,后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中予以全面确认。但这些法律文件并没有就隐私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主流观点认为,隐私又可以称为生活秘密,是私人生活中不欲为人知的信息。[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将隐私等同于秘密,因而这种观点又可称为秘密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汉语词典中,对隐私的界定亦是采用此种观点。[7]
在秘密说的要义下,一旦个人的信息被公开,那么这部分被公开的信息将不再属于隐私的范畴。这种观点之所以能成为主流,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隐私一词系近代翻译而来,最早与阴私同等使用,[8]而阴私一般指不宜为外界所知的与男女两性关系有关的生活秘密,[9]因而非公开性是隐私的最初要义,同时这也是中国法律在未有规定隐私权时,司法机关参照名誉权的保护方式来保护隐私利益的原因所在4。秘密说延续了隐私解读的传统做法,但是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非公开性系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产生的,由于信息传播的不发达,即使权利人对特定人公开其信息也不足以影响其正常生活,非公开性已足以实现隐私权设立的目的。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观点的局限日益显现。
(二)中国隐私权保护的传统模式分析
由于法律设立隐私权时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尚未成熟,因此在隐私权的保护上中国主要以秘密说为指导,具体而言,中国的隐私权保护主要以“公开/隐私”的二元模式为主,在该模式下,一旦权利人的信息被公开,那么该公开信息将不再属于隐私的范畴,因而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虽然法律对此未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却在司法判例中有所体现5。总的来说,在传统模式下,中国的隐私权保护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体具有特定性。一般而言,隐私权保护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等集体组织。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隐私权是体现人格利益的权利,而且也在于法人等集体组织的相关信息一般与公共利益有关。例如,就企业法人而言,如果将其商业信息认定为隐私权客体,那么其易于借隐私权的理由而掩盖其产品质量低劣、服务水平低下等情况,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10]此种主体的限定凸显了秘密说的本质,因法人等集体组织的相关信息事关公共利益,所以这些信息不能予以保密,只能向社会公开,故不属于隐私的范畴。
第二,保护的客体具有非公开性和私人性。所谓的非公开性,主要是指隐私权保护客体的隐私利益是个人没有公开的信息、资料等,是公民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道的个人的秘密。[11]非公开性是秘密说的应有之义。正是基于此,中国传统模式仅将隐私限于不为外界所知的非公开信息。而私人性意味着,隐私权保护的客体只能是与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无关的纯粹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信息和事务。[4]正是由于这些信息与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无关,因而权利人才得以对此进行保密,这种做法,亦是秘密说的体现。可见,基于秘密说而衍生的非公开性是中国隐私权传统保护模式的本质特征。
第三,隐私的利用体现人的自主性。隐私信息事关权利主体的生活安宁、个人自由,隐私信息的公开将使权利人的一切为他人所知,这容易导致权利人在做出决定时受制于知悉其隐私的人,最终造成的后果是,权利人的生活不再自由,不再安宁,不再是自己的主宰,并丧失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2]因此,自主性是隐私权设立目的的应有之义,权利主体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及何时公开其信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网络技术为手段的侵权案件逐步增多,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3日出台了《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用以规制实践中日益增多的网络侵权案件。其中,在第12条规定了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保护,明确了不构成侵犯隐私权的情形,而其中包括“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情形。这种情形从实质上来说仍沿用原有的保护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的延续性和衔接性,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做法无疑减损了权利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权,无助于从根本上实现隐私权设立的目的。
互联网时代传统隐私权保护模式的局限
(一)互联网技术的特点
互联网技术始于1969年的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最初仅作为通信工具使用,直至21世纪,其在中国的发展才真正达到迅猛状态。[12]由此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的侵权案件逐步增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特点一: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互联网的虚拟性,意味着它与现实世界存在差异,互联网的使用者难以从已有的经验中判断其他网络用户信息的真实性,因而它带来了与在现实社会中完全不同的体验。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在互联网的虚拟环境下,很多人在上面说话放得开,甚至为所欲为,而在现实中,他们会收敛很多。”[13]
特点二:互联网具有交互性。互联网的交互性,意味着网络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选择信息和交流对象,并根据对方的信息或活动立即进行信息反馈或相应的行为。[14]交互性为信息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主体只要将信息置于互联网中,那么这将意味着他人可以随时获得该信息,并可迅速传播给下一个接收者。
特点三:互联网的数字化。数字化是互联网技术的重要特征,在此之下,置于互联网上的信息均表现为数据形式,使得一切网络活动最终也都表现为数字。[14]数字化使得网络不仅可以在空间上储存海量信息,而且在时间上能把这些信息永久储存。这在为网络用户获取信息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信息主体的权利带来被侵犯的风险。
(二)传统隐私权保护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正是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信息主体的隐私权被侵犯的风险加大。然而,立法不仅没有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反而仍沿用原有的做法,以秘密说来界定侵犯隐私权的责任标准。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不特定的第三人将可以合法地侵犯信息主体的隐私利益,这无疑与隐私权设立的初衷相违背。在互联网时代,传统隐私权的保护模式日益凸显其局限性。
局限一:难以保护主体的隐私自主权。隐私的自主权主要体现在权利人对隐私利益的控制上,然而,互联网技术所特有的属性,不仅使个人的信息能够很容易地被永久记载于网络中,而且也使得个人的信息能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上传播,这无疑会超出权利主体的控制范围,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如果我们只想用短链接将信息拴住的话,将会有许多事情逃出我们的控制。”[15]囿于传统思维,当前的隐私权保护模式凸显脱机时代的特色,个人只要自行公开其信息,那么这部分公开的信息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权利人自行在网络中公开信息,那么他将失去对公开信息的控制权,第三人将可对其进行肆意的传播利用,即使信息的传播可能违背权利人的意愿,第三人也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局限二:难以保障主体的生活安宁。在传统隐私权保护模式之下,公开的信息不再属于隐私的范畴,这也意味着第三人将已经在网上公开的信息进一步传播,并无需负侵权责任。这无疑间接地鼓励网络用户传播他人的公开信息,而互联网的特有属性,使得这些信息能够迅速蔓延。由于传统隐私权保护模式系在脱机时代中产生,因而其所忽视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权利人对信息进行公开并不意味着他要让不特定的第三人都知道该信息,将他人在网络中公开的信息做进一步的传播无疑会给权利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例如,前段时间美国脸谱网饱受诟病的“新闻供应”功能,当用户在他们的空间中添加信息时,该服务会立即通知此人的所有朋友,这导致用户的一举一动都为他人所知,致使用户的询问来电不断,给用户的生活带来困扰,因此这项功能在用户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15]在传统隐私权保护模式下,脸谱网的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即使用户反对,脸谱网也可以置之不理。这种结果无疑从根本上违背了隐私权设立的目的。
局限三:难以维护主体的自由。如前所述,基于互联网的特有属性,一旦权利主体在网络上公开其信息,那么这部分信息将容易为不特定的第三人所知,这在间接上无疑使权利主体在网络中沦为“透明人”,导致其在实施任何行为时都要再三思索,这对于个人的自由权利而言是极大的束缚。此种情形正如美国著名的互联网法律专家雷西格所言:“网络空间并不保障自由,反而非常有可能使之受到控制。”[15]
局限四:难以维护主体的利益。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与个人有关的信息财产价值日益凸显,例如香港八达通公司曾将其客户的个人信息进行出售,获利4400多万港元。[16]正是基于此,在全球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公司,例如美国的Double Click and I-Behavior。而互联网技术的特有属性,正为这些收集行为提供极大的便利。在中国传统隐私权保护模式之下,公开的信息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这意味着,第三人将可利用网络的便捷条件,对他人公开的信息放心地进行收集使用,因此而获利却不用承担侵权责任。而信息主体由于没有权利基础,因此其无法向获利者要求分享利益。这不仅使信息主体的利益遭受合法的掠夺,同时也使隐私的控制权受损。
唐山华业私家侦探公司专业提供婚外情调查、寻人寻物,债务追讨等业务。
唐山私家侦探:网络时代如何保护自己隐私
来源:唐山侦探公司 时间:2018-03-15 16:50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