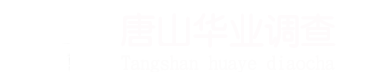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
(一)本罪客观行为认定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修订的表述,“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称为本罪。根据现行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表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两种类型的行为方式:出售、提供型和非法获取型。从表现形式看,这两类别的行为都属于作为形式的犯罪。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非法获取型规制的是行为的获取阶段,处于上游:而出售、提供型规制的是获取的后阶段,处于下游,且是针对合法获取到的信息的出售和提供。尽管两类行为的处罚相同,但是对于两类不同的行为,刑法对其分别规定,既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实质要求,也有助于人们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合理的预期。在个人对自己行为有明确的预期之后,有利于规范个人的行为,从而实现立法的初衷,保护个人的隐私。
(二)本罪主体方面认定
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即“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学说笔者现在尚且不能断定何种学说更为正确,但通过对比两种学说,笔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肯定说认为国家机关具有形成自己意思的能力,其形成犯罪意思的时候,国家机关不是国家意志的代表,因此国家机关是可以沦为犯罪工具,不能仅因在司法角度上无法对国家机关审判而否认国家机关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否定说”则认为国家机关是代表国家意志进行活动,与犯罪意思是对立面的。由此得知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坚持将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做法,因为在随着当今这个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到来,国家职能机关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全方位的收集和处理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国家机关在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明确犯罪主体是必然之事。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法不足与改进
(一)个人信息保护不足,明确范围
个人信息无所不包会影响到刑法对其的保护,因为过于宽泛的标准并不具有实操性。虽然在日常用语的习惯上,我们通常将出售和提供行为归属于利用行为的一种,但是刑法用语毕竟不同于日常用语,所以我们不能类推的将出售和提供行为在刑法上定性为利用的行为。武汉大学的皮勇教授指出,判断公民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首要考虑该信息与公民的重大人身、财产法益是否具有紧密关联性。若是有关联性,则考虑信息保护。若是紧密关联性不大,则考虑信息共享。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立法,将公民的个人信息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进行界定,再结合我国已有的网络安全法等规范,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明确界定。
(二)主观犯罪过失有所欠缺,增加过失犯罪
从实然的角度來说,过失不构成本罪。原因在于在传统的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法益的重要程度不及生命健康权,甚至财产权重大。所以刑法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过失犯非难程度较轻,在处罚方式上秉承着对过失犯处罚例外的原则。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逐渐提升,使得个人信息权成为新的重大法益。在应然的角度,过失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因其同样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应当被罪犯化。因笔者认为增加过失犯罪的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法益不被侵犯,然而即便是过失行为同样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并不能因为是过失行为导致,就能减免其危害后果。因此,过失导致侵犯公民信息权的行为也具有刑法处罚的必要。近年来频发的公私机构因不慎泄露公民信息而给信息主体招来危险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悲剧的发生足见过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发生的高度盖然性。将过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本罪的构成,一方面可通过刑罚的方式督促相关义务人,另一方面也能实现事后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事前预防。
华业唐山侦探公司拥有专业的唐山私家侦探,唐山私人侦探调查团队,提供唐山婚姻调查,唐山外遇调查等服务,成立多年博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是值得点赞的唐山侦探公司。了解更多服务请登录【官网】http://www.tszhentan.com 进行了解。
私人侦探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
来源:唐山侦探公司 时间:2018-12-02 10:05 点击:
-
上一篇:唐山私人侦探谈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下一篇:建筑工地工程款清欠问题研究